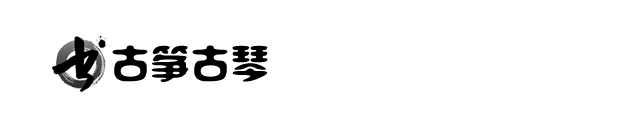当几内亚湾的朝阳把海面镀成琥珀色,中港疏浚公司“航浚6009”轮的机器轰鸣声,正奏响清晨的序曲。崔瑞长摘下防晒面罩,海风雕刻出他棱角分明的脸庞,眼角细纹里嵌着未干的盐霜——这是西芒杜航道给所有建设者的“勋章”。作为退役炮兵班长,他常挂在嘴边的理儿朴素却坚定:“不管是当炮兵还是做操耙手,差之毫厘,就得谬以千里。”

几内亚项目航道的海床像一块被岁月磨砺的巨型磨刀石。铁帽石藏在水底深处,冷硬的棱角在暗流中闪着光,17吨重的耙头撞上它,常被扯得耙齿连根断裂,发出刺耳的嘶吼。硬质黏土层同样难缠,像熬稠的糖浆裹住耙齿,连耙头格栅的钢铁关节都透着吃力。崔瑞长的工作,就是和全船18名同事在这片“雷区”里并肩作战,“啃”出一条长22.70千米、宽250米的几内亚“黄金通道”。

“老崔操耙,比打靶还准。”二副潘文博对今年那场暴风雨仍心有余悸。当时船舶在5级风浪里像片倾斜的树叶,耙深突然失控,屏幕上的红色曲线仿佛惊慌的蛇般冲出安全区。崔瑞长的双手在疏浚操控台上翻飞,精准地控制着操纵手柄,指腹因用力而泛起白痕,手臂肌肉紧绷如拉满的弓——这是他多年以来的“看家本事”。60秒后,曲线稳稳回位。他抹掉额头的汗水,喉结微动:“耙头就是我的炮口,风浪再大,也得咬住目标。”
每半月一次的燃油补给,是对船员技术与胆识的“联考”。加油海域看似平静,底下却暗流涌动,“航浚6009”轮与供油船像两个在风浪里摇晃的“醉汉”,要在颠簸中完成安全绑靠,这活儿被船员们戏称为“海上穿针”。

4月的那次补给,让属地化员工忍不住频频竖大拇指。涌浪推着两船忽远忽近,崔瑞长站在船艉,目光像雷达般锁定对方甲板的缆桩,指节因攥紧拳头泛出淡青色。当两船距离缩到近30米时,他突然抬手,二副潘文博心领神会喊出“抛”字。撇缆头划出的弧线,“啪”地精准落在指定位置。从撇缆绳抛出到系缆完成,再接上输油软管,全程仅用9分23秒——船长王世华在驾驶台掐着表,把这个数字记进了工作日记。

“这手预判,是长期练出来的。”崔瑞长一边整理绞缆盘上的缆绳,一边笑着说。长期的训练,让他能在30米外让沙包稳稳落进直径1米的圆圈。如今测算两船的相对位置、速度和涌浪周期,不过是把抛物线公式换了个应用场景。缆绳整理妥当,他又和同事陈治萄钻进泥舱疏通高压冲水喷嘴,铁锈混着泥浆溅在工装上,像幅随性的抽象画。“这些细节,少擦一下都可能出岔子。”他拍了拍工装说。
几内亚项目的施工环境堪称恶劣,疏浚设备的磨损程度远超想象。崔瑞长每次起耙上架后,必给设备做“体检”:从耙臂弯管到耙头,从液压管接头到每一根螺栓的紧固部位,连锈迹下藏着的细缝都不放过。“报告驾驶台,耙齿更换1个,已安全返回生活区。”类似的对讲机汇报,他每天要说不下五次,声音里总裹着海风打磨出的沙哑。

今年三月更换耙管波纹管那天,甲板温度飙过40℃。崔瑞长和同事晁小永站在甲板上,在大副王坤的带领下配合得严丝合缝。阳光直射处,气动扳手的震动震得他虎口发麻,汗水顺着安全帽系带淌进衣领,在工装后背洇出一片深色“地图”。政委王燕军递来矿泉水:“炮长,你们歇会吧!”他微笑着摆摆手,扳手转动的角度依旧分毫不差,连齿轮间隙都得卡着指尖量准分寸。

“你们这速度,快赶上咱们船的螺栓拆卸纪录了!”王燕军拍着崔瑞长的肩膀打趣。他只是嘿嘿笑,手里的活没停。心里清楚,这条“黄金通道”早一天贯通,几内亚的矿砂就能早一天运向世界。有次和女儿视频,小姑娘举着课本里的“一带一路”地图问他在哪,他指着屏幕里的航道图笑道:“爸爸在给大船开路呢,就像当年在海边站岗,守护着一条通往远方的路。”

夕阳西沉时,崔瑞长总爱站在船艉。航道在船后铺展开扇形泥浆带,像一条正在凝固的金色绸带,在暮色里泛着微光。不远的将来,万吨级矿砂船将沿着这条“黄金通道”驶向世界,而他手掌的老茧、工装上的盐霜,早已成了这条“一带一路”纽带上鲜活的中国印记。